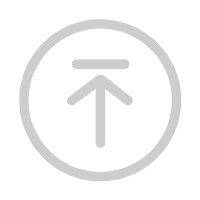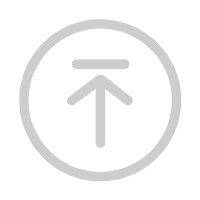


10月28日上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文飞教授为我们带来一场无比精彩的论坛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俄国书刊审查制与俄国文学中的“伊索式语言”。刘教授分三个方面对这个题目进行详细的讲解。
报告中的刘文飞教授
首先,刘教授概述了俄国书刊审查制的历史。俄国文学的历史通常自公元12世纪末的《伊戈尔远征记》算起,可在此前一百年俄国便出现了第一份禁书目录1073年的手抄书《斯维亚托斯拉夫抄本》,这便印证了纳博科夫的小说《天赋》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俄国,书刊审查制的历史要早于文学……”彼得时期制定的《宗教法则》提出设立专门机构,被视为俄国书刊检查制的首次尝试。叶卡捷琳娜登上王位后,起初以明君自居,与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通信,但是,当俄国文人群起而效之,纷纷办起讽刺杂志,当德国书商大量进入俄国,开始印制各种图书,思想界一时大为活跃,叶卡捷琳娜女皇开始感到不安甚至恐惧,便实施了空前严厉的言论控制,于1783年颁布《自由印刷所法令》。规定所有书稿必须提前送交警察局审批。在俄国延续达两百年之久的书刊审查制度从此确立,“цензура”的概念从此被引入俄语,拉季舍夫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受到了首次的查禁。亚历山大一世时期,1804年颁布的《书刊审查法案》内容却相对宽松,它宣布放松外国书刊的入境限制,重新允许设立私人印刷所。但是,皇权至上和出版自由之间永远存在矛盾,最后还是将审查权交给了警察局。尼古拉一世是俄国历史上最为多疑、最为专横的君主之一,他在位的30年(1825--1855)是俄国历史上思想控制最为严格的时期,他授意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对1804年《书刊审查法案》进行修订,此修订稿因其严酷后被史家称为“铸铁法案”,不仅严格限制即将或业已面世的出版物,而且还试图介入并控制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学进程自身。19世纪下半期就总体而言是一个相对宽松的出版时期,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后不久便顺应历史的意愿着手废除农奴制,为此展开一系列放松思想控制的举措。20世纪之初,在1905年革命和日俄战争等事件相继爆发之后,内外交困的沙皇政府被迫在内政方面作出一些让步,在书刊审查方面也体现出更多怀柔。然而,在1906--1916年的10年间,还是有近1000本书被销毁,其中大多为鼓吹革命的政论作品,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政府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强化了舆论监督。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临时政府实施空前宽松的出版政策,各种形式的书刊审查完全消失。十月革命后的整个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着或明或暗、时松时紧的书刊审查制度。1922年,先前隶属于宣传、政工、出版、警察等不同部门的书刊审查力量被整合为一体,成立“出版事务总局”。整个30年代,伴随着政治和社会上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苏联的书刊审查制度空前严厉和残酷,成千上万的创作知识分子因为其作品获罪。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出版政策先松后紧,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在东西方冷战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俄国历史的“钟摆法则”再度显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公开性”,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诸文化领域的开放和透明。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出版和其他信息媒介法》正式宣布禁止任何形式的书刊审查,允许私人开办出版社、印刷厂、报刊和各种信息媒体。
其次,刘教授深入浅出地对俄国书刊审查官的形象做出详细的剖析。他借用克拉索夫斯基的例子揭示了俄国书刊审查官如何成为俄国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负面形象。刘教授强调,纵观俄国文学的历史中书刊审查官,无论他们的身份和心理还是他们的处境和作为,都体现出了某种饶有兴味的复杂性。第一,俄国书刊审查官的构成本身就是复杂的,他们中间既有糊涂判官,也有饱学之士,甚至不乏杰出作家。客观地说,无论在哪个时代,能被当局挑中担任书刊审查官的人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甚至相当深厚的专业知识。俄国文学史中的许多大家,如维亚泽姆斯基、谢·阿克萨科夫、丘特切夫、冈察罗夫和迈科夫,以及苏联时期的谢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卢那察尔斯基等,均担任过书刊审查官。第二,作为一个集体的书刊审查官,其形象无疑是僵化刻板的,可悲可笑的,但作为个体的书刊审查官,其生活和工作则可能是丰富多彩的,充满戏剧性突转的。第三,俄国的书刊审查官与俄国书刊审查制度自身一样,无疑是出版自由的敌人,文学发展的掣肘,但作为个体的书刊审查官,其所作所为却往往也因人而异。所以说,俄国书刊审查官只是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的门卫而非其主人,作为文化警察和文学猎犬,他们是俄国作家和文化人天然的敌人,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他们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在以某种奇特的方式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此外,刘教授对文学中“伊索式语言”做了概要的综述。所谓“伊索式语言”,就是俄国书刊审查制作用于俄国文学而产生出的一种结果。这一概念最早由谢德林在19世纪60--70年代引入,它得名自古希腊寓言家伊索,意指一种为了骗过书刊审查官而采用的“寓言体”文字,一种通常具有嘲讽和批判意味的委婉的、伪装的思想表达方式,一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修辞手段。从规模上看,“伊索式语言”可大可小,大可至整部长篇小说,也可能小可至一个语言单位,一个句子,一个单词,甚至一个小小的标注。从语言学的分类上看,“伊索式语言”既是语义层面的,也是语用层面的。语义层面的“伊索式语言”,主要借助双关语、同音词、同义词、潜台词等手段实现语义的微妙转换;而语用层面的“伊索式语言”,则离不开由具体的时代和社会、文化和典故、风尚和禁忌等等构成的特殊语境。“伊索式语言”在题材和体裁上的体现方式也十分多样。从题材和情节上看,“伊索式语言”最常用的方式有以历史为借鉴,让不同时间单元中相近的人和事形成对比,从而构成某种暗示;以异域他国为假托,利用偷换地理空间来混淆视听,即所谓以彼处喻此地;以幻想情节为遮掩,其中包括科学幻想小说和其他类型的幻想小说,情节常常被设置在未来;以动物或植物为描写对象的自然题材小说,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被视为这一体裁的代表作,但在俄国文学中,始自克雷洛夫的强大的寓言写作传统就某种意义而言均可归入此类;假托儿童题材等。“伊索式语言”本身自然就可以被视为一种体裁,比如,寓喻法,戏仿法,迂说法,省略法,用典法,笑话法等。在更多情况下,这些修辞方式或曰微型体裁往往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任何一种语言修辞方式和文学表达手段均可以被有心的作家用作他别有深意的“伊索式语言”。
最后,刘教授对本次报告做了一个小结。俄国文学史中的每一位著名作家都曾程度不等地遭遇书刊审查制的迫害,俄国文学史中的每一部著名作品都曾或多或少地遭遇书刊审查官的刁难,一部俄国文学史,竟然成为一部俄国文学与书刊审查制、俄国作家与书刊审查官不断冲突和斗争的历史。但从洛谢夫的专著《书刊审查制的益处:现当代俄国文学中的伊索式语言》的题目本身便不难看出,其作者所言之俄国书刊审查制的“益处”主要就体现为“伊索式语言”的生成和广泛运用。除了这个益处之外,俄国书刊审查制无意之间将“时代先知”和“社会良心”的角色赋予了俄国文学,使俄国文学在俄国文化中赢得了所谓“文学中心主义”的角色。俄国书刊审查制也以某种奇异的方式保持着俄国文学的“生态环境”。书刊审查制的存在,客观上使文字的发表变得不那么容易了,这便变相地向作家们提出更高的写作要求,要求他们掌握更高明的写作技巧,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伊索式语言”的字斟句酌,冥思苦想。俄国书刊审查制和俄国文学像两条不时相交的平行线,“伊索式语言”在其中穿针引线,三者共同织就俄国文学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它们又构成一个文化三角形,象征着体制、文学和语言这三者间的对峙和妥协,角力和转换,这一过程同时也折射出了谢德林所谓“俄国艺术的独创特征”。(常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