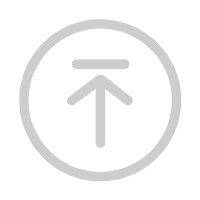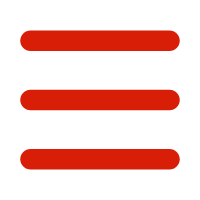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嬗变
第21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古希腊文学与思想史”系列讲座②
2022年10月18日晚18点,应4166am金沙信心之选邀请,海南大学社科中心教授、中国古典学学会常务理事程志敏老师,为我院师生做了主题为“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嬗变”的讲座。本次讲座入选第21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系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52讲。讲座由英语系罗峰副教授主持,逾300名校内外师生以腾讯会议的方式线上参与。

程志敏教授著述众多,贯通中西古今,已出版《荷马史诗导读》《历史中的修辞》《古典正义论》《西方哲学批判》《归根知常——政治哲学的古典面相》等专著10部,另有《苏格拉底的申辩》《宙斯的正义》《柏拉图〈克力同〉章句》《柏拉图的哲学》《弓与琴——从柏拉图解读荷马》等译著13部,研究范围涵括了古典诗学及政治哲学。在引言中,罗峰老师提到,普罗米修斯这位古希腊神话人物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好些作家都在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语境里重述了普罗米修斯神话。普罗米修斯在历代作家笔下呈现出多重面相。普通读者对普罗米修斯的了解,大多是通过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及浪漫派诗人雪莱与之针锋相对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更熟悉古希腊作家的读者可能还知道,普罗米修斯还出现在了赫西俄德《神谱》《劳作与时日》及柏拉图对话《普罗塔戈拉》中。程志敏教授将通过细致梳理普罗米修斯在西方思想史上形象的嬗变,为我们逐步揭开这个人物的神秘面纱。
程志敏教授在报告中分四部分呈现了普罗米修斯在思想史上的形象流转:普罗米修斯的普遍形象、现代形象、古典形象和古风形象。讲座开始,程老师就指出,四个部分中的前三部分实际上很接近,都涉及普罗米修斯广义的现代形象,真正的区别在于普罗米修斯最后的古风形象。
程志敏教授首先从鲁迅先生谈到马克思对普罗米修斯的看法,梳理出其普遍形象:最高尚的圣者和训道者。鲁迅先生称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的精神”,视其为“博大坚忍”的革命者。程老师认为,普罗米修斯就是鲁迅先生笔下“为民请命的人”——普罗米修斯乃是“人类的脊梁”。程老师随后提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序言中指出,普罗米修斯代表着“哲学、批判和反抗”。普罗米修斯的反抗代表着哲学征服世界和对绝对自由的追求。而普罗米修斯所谓的“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的自白和格言。普罗米修斯的现代形象与这里的普遍形象可谓一脉相承。
接着,程志敏教授主要从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入手,解析了普罗米修斯的现代形象。出于对埃斯库罗斯让宙斯与普罗米修斯和解这一结局的反感,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直接修改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让“人类利益的维护者(普罗米修斯)与人类利益的压迫者(宙斯)”永不和解。雪莱眼中的普罗米修斯俨然成了“道德与智力”最完美的典范,受最真最纯的动机驱使去追求最崇高的至善的目标。雪莱的这一看法实际上主导了现代人对普罗米修斯的普遍看法。雪莱试图通过塑造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满足“改造世界的欲望”,而库里亚诺批评说,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让我们“听到了现代虚无主义分娩时的阵痛”。
德国思想家谢林同样认为,普罗米修斯把理性与意识倾注到人类身上,将凡夫俗子拔高到了神的高度。歌德在短剧《普罗米修斯》中亦重构了古希腊神话:宙斯成了普罗米修斯的父亲,而潘多拉成了他的女儿——歌德实际上彰显并高扬了当时德国的“狂飙突进”的文化精神。
在谈及普罗米修斯的古典形象时,程志敏教授首先表明了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的三处疑问:首先,该剧把神王宙斯塑造得很不堪,这与埃斯库罗斯其他剧作中的宙斯形象大相径庭;其次,剧中歌队的出场顺序不符合当时的戏剧惯例,学界对于该剧是否埃斯库罗斯原作依然存疑;埃斯库罗斯与赫西俄德对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塑造何以迥异。
在分析中,程老师特别指出,“爱人类”(philanthropia,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之一“博爱”及我们熟知的“慈善”即源自该词)一词实际上最早出自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剧中塑造的普罗米修斯赋予人类一切技艺,把“盲目的希望”送给人类,使之不再能够认识死亡,更可能与天神争胜。为了启蒙,宙斯必须被塑造成一个“恨人类”的僭主。“秩序成为奴役,破坏秩序被视为追求自由”。在此,程志敏教授提出理解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关键问题:埃斯库罗斯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埃斯库罗斯是保守主义者,《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则堪称警世之言;若他是启蒙者,那么普罗米修斯就是一个大无畏的革命者。
关于普罗米修斯在剧中犯下何种罪行的问题,程老师表示,普罗米修斯真正的罪并不在于盗火,而在于由理性支持和怂恿滋长的肆心傲慢,导致他不懂得节制。普罗米修斯清楚自己的罪行,但他“似乎别无选择”。作为读者,只关注正义的宙斯与过分爱护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可能都正确,但也可能都有失偏颇。因为二者皆因“过度”导致神与人、公与私的绝对对立。这“一曲之偏”恰恰构成了真正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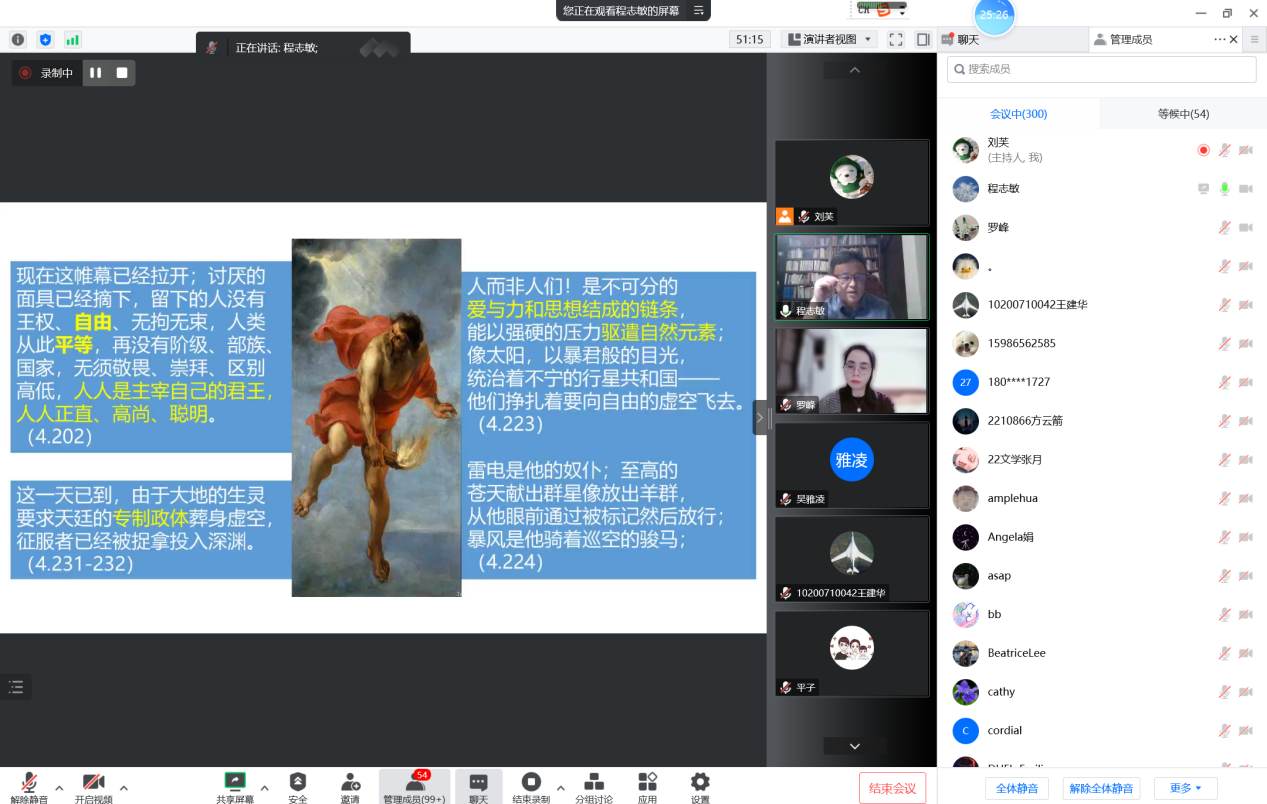
在第四部分,通过回溯普罗米修斯的古风形象,程志敏教授提出,普罗米修斯形象嬗变的古今之别,核心在于埃斯库罗斯与赫西俄德的差异。他还特别提醒,我们通常认为的古今之争似乎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实际上彰显的是“品质的区分”。赫西俄德笔下的宙斯不是暴君,普罗米修斯也未表现出对人类的过分偏爱,更未给予人类“盲目的希望”(“希望”还在潘多拉的魔盒里)。换言之,彼时的普罗米修斯尚不具有革命与启蒙的含义。赫西俄德笔下普罗米修斯的原罪在于他是提坦族成员,威胁到宙斯的统治,盗火不过是他实施惩罚的借口。
在赫西俄德那里,如果普罗米修斯不盗火帮倒忙,宙斯进行公平分配,人类就不会落入后来的惨境。宙斯旨在维持秩序,而普罗米修斯却通过反叛宙斯导致人神分裂加剧。正如伊利亚德所说,赫西俄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非但不是人类的英雄,反而要对人类的堕落负责。程老师随后通过对比培根,反思了普罗米修斯代表的“理性欲望”存在的问题。在培根笔下,普罗米修斯试图玷污雅典娜,象征着理性对神性和自然的玷污,而这正是现代人类面临的难题。但程志敏教授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像现在普遍的做法那样过分拔高普罗米修斯。在古希腊,普罗米修斯也并非显赫的主神,而只是诸神中的一员,他在希腊的地位也并不高。
程志敏教授在讲座最后强调,从思想史上来看,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复杂多面,我们不能用扁平形象看待这一神话人物。

在评议环节,来自上海社科院的吴雅凌研究员表示赞同程志敏教授对普罗米修斯问题的基本判断。程老师用丰富生动的例子呈现了普罗米修斯贯穿古今始终鲜活的形象,深入探讨了这一形象嬗变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史的问题意识。普罗米修斯从古希腊最早文献中的配角摇身变成主角,渐渐活成了现代世界的英雄,有时甚至还是某种反英雄。古今之争的问题意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提问:普罗米修斯形象里的什么根本性的东西使之常葆持续生命力?
吴雅凌老师指出,赫西俄德《神谱》的主角是宙斯。诗人用最好的修饰语称呼至善至高的神王宙斯。普罗米修斯故事只是神王战功的一部分,与宙斯对战提坦、提丰等篇章相辅相成,旨在言说某种名为奥林波斯的世界秩序或某种整全的宇宙论。这是赫西俄德的传统,也是荷马及其追随者(如托名荷马颂诗)的传统。在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那里,宙斯作为主人公的言说方式在现实中显得不够用了,普罗米修斯进而代表一种自主知识的属人的努力,以及由此引发的僭越和付出的代价。事实上,在赫西俄德本人那里也已出现分离。有别于《神谱》,《劳作与时日》的历史时间是黑铁时代,赫西俄德让不同于传统英雄的小人物成为诗歌的主人公,但他保留一点,通过在序歌里呼唤宙斯,让宙斯的目光在全诗中无处不在。当我们思考从古到今没有断过的普罗米修斯挑起的文明问题时,不妨试问:我们心系的是哪一类主人公得以站立其中的哪一种世界秩序?
在互动环节,程志敏教授和吴雅凌研究员就参与者提出的关于浪漫派诗人与普罗米修斯的关系、普罗米修斯代表的理性和宙斯代表神性对抗的关系、荷马史诗中译本及《神谱》中的提坦形象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图文 | 刘芙、罗峰